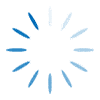……这是在说什么?
这本书还是用渊深曼达安语写的,天知道他磕磕绊绊翻译出来的时候有多怀疑自己这门外语是不是白学了。
不过学了用处也不大就是了,反正他没看见哪个景区告示牌是用渊深曼达安语写的。
工藤新一将头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整理思绪。
现在这种程度他倒还勉强应付得来,只是这样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研读翻译、书房被各种书籍文献塞满的情况,似曾相识得让他稍感不适。
工藤将椅子转向门的那面,端详房间现在的样子。
如果收拾得再整齐一点,就跟当年片山翼那个挤满了书的书房没什么两样。
将时间投放到没兴趣的事业上是种折磨……也可能是因为这部分所吞噬掉的精力实在太多了。
短时间自学六七门语言到能读书的地步,然后再从那些晦涩的字句中扣出蛛丝马迹、片山翼是不是还在空闲时候打了两份工?
对,兼职……她甚至还兼职!
原本调查片山翼在米花町的情况时,她所展现出的冷漠还让人难以理解:不管是被炸弹的音浪掀翻后继续爬起来骑自行车回家、还是路过命案现场连眼神都不给一个……
现在工藤新一多少能理解了,当人精力被压榨到一个限度时,受生理构造限制,就是会表现出惊人的冷漠。
片山翼简直是以怪物般的意志力、七年来每天努力从血肉中挤出第25个小时来。
工藤新一不想放弃的原因除了一点胜负欲外,更多的是探求心。和一些充满矛盾的宗教故事不同,密教书里的内容几乎全是合乎逻辑的(尽管不是正常逻辑),它们的存在能解释许多问题。
但是,想把这些东西用一两年的时间看完太难了。就算还有个有名怪盗和他一起研读,但他们两个人毕竟不是能互相继承进度的机器,齐头并进的进展比独自研学快不了多少。
书店那边说是没有时间限制,工藤新一没傻到会信以为真。
光那时候的形式就能看出来,片山翼绝对是给不知道多少人发出了邀请,谁先写完谁就先交卷离场。
工藤新一不知道名额究竟有几个,也不知道在这个无形的考场里坐了多少看不见的对手,就这样在纸笔不停书写中度过了进入大学以来的时光。
最近他开始考虑换其他方法,如果继续将时间大把大把投入进去,他和片山翼又有什么区别?
“嘀——”
他在望着房间的书山出神时,电脑突然响起收到新邮件的提示音,发件人宫野志保,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
【水无小姐回美国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
看清这句话的瞬间,工藤猛地坐直了身体。他快速将这句话来回读了两边,然后匆忙将纸笔和没看完的书都摞到角落,想方设法求证这个消息。
感谢时差,他联系的人回消息都很快,不到一会儿就确定这个消息属实。
水无怜奈(本堂瑛海)半个月前返回美国,并且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尽管不清楚是例行公事还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这都是一个危险信号。
片山翼离开日本时带走的几乎都是活死人、没有在她控制下的只有水无怜奈。
片山翼从国外巡游一圈后再回日本的可能性极低,现在队伍里唯一的正常人离开了,她很大概率是要有什么大动作。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无论多危险,他都必须赶快采取行动。
工藤新一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
两天后,斯洛伐克。
工藤新一落地不久,布拉迪斯拉发就开始下雨。等他收拾好东西从落脚的地方出来时,外面已经是晚上,车灯与霓虹招牌经过水汽折射,给人以朦胧迷离之感。
街上的行人数量太少了,外地人更是几乎看不见。
工藤新一裹紧了外套,他不确定这股冷意是因为降温、还是来自当地人那些自认为隐蔽的打量目光。
这种紧张氛围只有少部分是因为显眼的亚洲面孔,更多原因在于前天发生的/总//理遇刺案。
原本这座中欧小城是让人感到惬意的旅游城市,但自几年前开始就纷争不断,或许是受整个欧洲政局动荡的影响,乱子接二连三。
工藤匆匆走过鹅卵石街道,路过一尊只剩下脚的雕像,有个老头沉默地站在这尊残破的雕像前,很像战争电影中悲情的一景。
可惜这尊雕像前没有任何鲜花之类的悼念品,只立了告示牌,用斯洛伐克语和英语告知行人这里不久会彻底拆除、请注意安全。
工藤收回目光,按照电子地图规划的线路来到跟人事先约定好的地点。
绝大部分餐馆这时间已经打烊了,那个人和他约好的地点似乎是一家特色旅店,这个时候仍然对外营业。
老板穿着巴洛克式的钟形裙,上面的机绣花卉图案因为盖了油污显得暗淡许多。她过来给工藤新一点单,开口说的是英语。
工藤新一点了餐,结果餐上来他完全没心情吃,食不知味地把东西往嘴里塞了两口,思绪发散。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