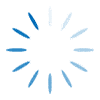宫里的雪,总是落得无声无息,像一层厚重的帷幕,将一切罪孽与隐秘都深深掩埋。天光映在琉璃瓦上,冷得透骨,四下寂静得仿佛连一丝呼吸声都能听见。
许安平从未想过自己会习惯一个人。可欢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成了他身边一道影子,一道他甚至未曾刻意留意,却已熟悉至极的影子。
晨起时,他总是早早地跪在殿门口候着,掌心托着温好的茶汤,手指微微收紧,怕烫到,却仍努力端稳;夜深时,他跪在许安平的榻侧,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柔声唤道:“殿下,您该歇息了。”他小心翼翼地等着,等着主子心情好时,才能将暖炉靠近,轻轻地捧起许安平的手,为他驱寒。
有时候,许安平会忘了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只当他是寝殿里某样熟悉的摆设——一件温顺、不会离开的东西。偶尔心情不错,他会随手扔给欢然一件旧披风,或是命人赏点药膏,治一治那些被鞭打留下的血痕。
欢然便会露出极淡的笑意,手指微微蜷缩着,小心翼翼地收起那些东西。他那双眼睛,总是湿润而温顺,看着许安平时,带着几分难以言喻的依赖。
宫中人人皆知,大殿下喜怒无常,脾性阴晴不定,稍有不顺便是暴怒相加。但欢然从未想过,自己竟能被他留在身边如此之久。
或许是因为许安平偶尔烦闷时,会让他跪在脚边,伸手揪住他的衣领,逼着他抬起头,冷冷地打量着,目光里似乎带着审视,又似乎藏着某种他不敢妄测的情绪。
或许是因为许安平偶然兴致来了,便会将他推倒在雪地里,俯身低笑:“你若真怕冷,就爬过来,抱着我的靴子。”
欢然便真的照做了。他向来顺从,从不忤逆。
那日,许安平提起某地蝗灾肆虐,饿殍遍野,百姓啼饥号寒。他只是随口一说,却不曾想,跪在榻旁的少年突然失了魂一般,颤着身子扑到他脚边,泪水扑簌簌地落在冰冷的地砖上,一遍遍哭诉着,想要回家去看看。
许安平那天心情很好,别人越是不幸,他便越觉得快意,于是随口吩咐下人去查探消息。
不过数日,消息便传了回来——
欢然口中那个遥远的村子,早已破败不堪,村民十去其九,余下不过寥寥数户苟延残喘。他的父亲,在卖了他之后,又将妻子和女儿典当出去,拿着银子不知所踪,从此音讯全无。
许安平倚着软榻,眼底一片漠然,少年瘫软在地的模样,在他看来只觉得好玩。
半晌,忽然伸手掐住了欢然的下颌,迫使他抬头与自己对视。少年双眸失焦,泪痕未干,整个人如坠冰窟。
许安平轻嗤一声,语气淡淡的,带着几分残忍的漫不经心:“你瞧瞧,现在这世上,能庇护你的人,便只剩下我了。”他笑了笑,微微俯身,唇畔几乎贴着欢然的耳廓,声音低沉,带着点近乎怜悯的冷意:“乖乖地做条狗。听话。”
那一刻,欢然终于明白,这世间再无他的去处。
他的家,他的亲人,都已在这场天灾人祸中化作尘土,而他所依存的唯一一方天地,便是眼前这个喜怒无常的男人。
从那之后,欢然愈发沉默。可也更加心甘情愿地跟在许安平身边。
哪怕这份庇护带着刀锋,哪怕这份依赖遍布伤痕,他都愿意承受。
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个人能让他依靠,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即便被辱骂,被责罚,被鞭笞得血肉模糊,他依旧不敢逃开,也不愿逃开。
他不敢想象,若是有一天,他真的被弃之如敝履,彻底孤苦伶仃,又该如何活下去?
所以,他只能依赖许安平。
依赖到骨子里,依赖到,再也无法挣脱。
新房沉静,红烛高烧,檀香缭绕,一切都透着一股静默而端庄的气息。
崔令仪端坐在喜床之上,等了许久,却始终不见新郎踏入房门。她不动声色,低头看着腕上的凤镯,神色平静得像是一潭古井,无悲无喜。
——而此时,宫殿深处,另一扇门被推开。
烛火微摇,照出偏殿里单薄而乖顺的少年身影。
许安平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跪伏在地的欢然。他眼底浮现一丝极端的满足感,步伐不紧不慢地走近,喜服外袍被他随意丢在地上,鲜红的衣角拖曳过冷硬的地砖,像是一抹妖冶的血色。他微微俯身,捏起少年的下巴,语气轻慢:“我成亲了。”
欢然低着头,眼睫微颤,手指死死扣着袖摆。那双曾经清澈无比的眼睛,此刻如同覆上了一层蒙尘的水雾。
许安平看着他,唇角缓缓勾起一抹笑:“你不高兴?”
欢然没有作声。过了很久,他才用极轻极轻的声音回答:“殿下成亲,是好事。”
许安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忽然拂袖一笑,语气轻蔑:“什么好事?本殿若愿意,她不过是个摆设。”话音落下,他屈膝坐下,单手撑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勾起欢然的发丝,指尖轻绕,像是在把玩某种他极为珍视的珍宝。
“欢然,你应当高兴才是。”
“本殿的婚事,与你无关。”
欢然心头猛地一震,蓦地抬起眼,眼底有一丝慌乱,一丝不知所措。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可最终却一个字都没有说出口。
许安平低笑着,指尖缓缓滑过他的脸颊,动作极尽温柔,声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本殿的宠爱,才与你有关。”
欢然膝行上前,许安平粗鲁地扯下裤子,压着他的头来到自己双腿间,吞吐舔舐,青涩却又小心翼翼。
成亲之后,许安平的性子并未改变,反而愈发偏执,占有欲如烈火般燃烧,恨不得将欢然锁在金丝牢笼之中,片刻不离。
“你是我的。”他常常这样说,语气温柔缱绻,目光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执念,像是对欢然的宣誓,又像是一道无法违逆的命令。
而欢然,终究是无法反驳的。他被困在这座华美森严的宫殿之中,挣脱不得,也不愿挣脱。因他从许安平的眼神里,看见了自己全部的归属,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占有,亦是一种无可逃避的深情。
可许安平对他的宠爱,并非无人察觉。朝中暗潮汹涌,几次朝堂之上,皇帝都曾言语敲打,暗指他后宫不修、行事乖张。更有御史上书,言辞犀利,指责他不入正室,反而专宠男伶,乃祸国之兆。
此事传入皇后耳中,她终于坐不住了。许安平的婚姻,是她亲自定下的,可如今,新婚之夜,他竟弃了正室,直奔一个身份卑贱的内监,这简直是对皇室颜面的践踏!皇后沉吟片刻,终究是冷笑一声,命人将欢然拖入宫内,罚跪于殿中,任由掌掴鞭打,直至满身伤痕,皮肉绽开。
殿门紧闭,烛火冷冷。宫人们按着他,硬生生将一卷白绫抛在他面前,语声冷硬:“奉皇后懿旨,内监欢然,行止不端,乱人纲常,赐白绫,速速了断。”
血腥味弥漫在空旷的大殿之中,白绫滑落在地,映着暗红色的烛光,显得无比诡谲。欢然依旧没有哭,也没有求饶。他缓缓抬眸,看向坐在高处的皇后,目光仍旧平静,仿佛一切早已命定。
许安平赶到时,正撞见这一地狼藉。大殿内,血迹蜿蜒,与被撕碎的衣物混在一处,从殿门一直铺展到冰冷的玉阶上。欢然被丢在地上,遍体鳞伤,单薄的衣襟破碎不堪,露出的肌肤上满是狰狞的鞭痕。他的手指死死扣着地面,像是还想撑起自己,可最终只是徒劳地颤抖着,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
许安平站在殿门前,周身沉入彻骨的寒意。他看着欢然,看着他伤痕累累的身体,看着他的血溅满地,看着他唇色惨白,仿佛下一刻就要断了气息。眼底翻涌起一片滔天怒意,胸膛剧烈起伏,掌心因过度用力而青筋暴起。
皇后懒懒地开口,声音淡漠,却字字诛心:“若你不愿夫妻共枕,本宫早晚有机会杀了他。”
许安平忽然明白了什么。纵然他手握权势,翻云覆雨,可权力再盛,也无法真正护住一个人。 他缓缓松开紧握的拳头,冷冷地看了皇后一眼,终是转身离去。
那夜,许安平第一次踏入崔令仪的寝宫。
建武元年的春日,宫中梨花盛开,宛如银装素裹的仙境,风儿轻轻吹过,花瓣纷纷扬扬,如雪花般洒落。百官齐跪于太极殿下,山呼万岁,金銮殿上的龙椅终于迎来了它的新主人——许安平登基,成为了这天下的至高之主。
新帝登基,举国同庆,万人朝贺,可唯独欢然只是静静站在殿外,目光深邃,望着许安平披上那身沉重的冕服。那冕服象征着权力与威严,而许安平的身影也在那一刻变得更加高远、陌生。他明白,许安平这一刻已经不再是那个只属于他一人的男人,而是这天地间,所有臣民的君王。
皇位虽加身,却并未改变许安平对欢然的宠溺。相反,许安平对他愈加宠爱如昔,甚至比之前更甚。新帝下旨,修建“摘星台”——一座金碧辉煌、直入云霄的宫殿,仿佛专为他而造。许安平亲自为它命名:“凡世间珍奇之物,皆当献于此处,让欢然一人独赏。”
天下的贡品、奇珍异宝,皆汇聚于此。有人说,摘星台里堆满了夜明珠,每到夜晚,整座宫殿都像是洒下了一片星河,闪烁着柔和的光,垂落人间;更有传言,许安平为了取悦欢然,甚至派人远赴西域,寻找异香异兽,只为博他一笑。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