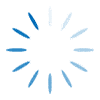欢然生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破碎家庭。母亲病入膏肓,父亲嗜赌成性,家徒四壁,唯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妹妹嗷嗷待哺。
他的名字是母亲取的,寓意欢欣安然,可惜,这份期许从未实现。
每天,他上山砍柴,回家烧水做饭,照料母亲和妹妹,日复一日,未曾有半句怨言。
他渴望读书,可家里穷得连一根像样的毛笔都买不起,便只能趁着空闲躲在私塾篱笆外,听着夫子和学童摇头晃脑地朗诵文章,跟着默默念上几句。私塾门前,他总是站得笔直,仿佛自己也是那堂中学子,可惜风吹雨打,无人容他。
村里那些男孩嫌他生得女相,不愿与他玩耍,女孩们又因他比她们还要秀美,心生嫉妒,时常在他劳作时恶作剧般地烧毁他的衣服。
欢然从不恼怒,亦不还口,他仿佛天生便是这般性子,安之若素,逆来顺受,活得像一株被风吹弯了腰的野草,卑微到尘埃里,却依旧活着。
他无暇多想,因为生活本就没给他留下思考的余地。
直到那天深夜,父亲醉醺醺地推开家门,浑身酒气扑鼻,随手将一袋碎银丢在桌上,眼皮耷拉着,高声说着:“我给你找了条活路,当个内监,换点银子回来。总比将来给你娶媳妇儿,还得搭上一笔钱强。”
屋内寂静得可怕,连风都似乎不敢灌进破旧的窗棂。
母亲听得这话,几乎是扑过去揪住了父亲的衣襟,眼里满是悲愤与绝望:“他是你的亲骨肉啊!你怎么能……”她话未说完,便被狠狠甩了一巴掌,整个人摔在地上,嘴角渗出血丝。
欢然连忙上前,将母亲扶起。他抬眸望着父亲,眼中看不出愤怒,甚至连一丝挣扎都没有。他轻轻拍着母亲的背,笑得温柔:“娘,我愿意去。”
母亲一瞬间哭得肝肠寸断,死死抱住他,泪水打湿了他单薄的衣襟。
可欢然仍旧笑着,那笑意淡如晨曦,毫无阴翳。他不知内监究竟为何物,只以为不过是被卖去某个富贵人家做苦役,签了卖身契,待攒够了钱,便能回家。
次日清晨,母亲亲手为他梳洗,指尖微微颤抖,却仍努力将他的长发细细梳顺,为他绾起发髻。破旧的铜镜里,少年眉目疏朗,黑白分明的双眸倒映着母亲泪眼婆娑的模样。他伸手抚去母亲脸上的泪痕,轻声安慰:“娘,你好好照顾妹妹,我以后赚了钱,常回来看你。”
宫门一入深似海,自此青天是梦中。
等到被人押入净身房,欢然才终于明白,父亲究竟是把自己卖来做什么的。叁十个孩子,被一并关在这阴冷的房间里,四周沉沉的木门死死封住了去路。净身房的青砖沁着百年的血气,药吊子咕嘟咕嘟熬着汤,苦味混着血腥在梁柱间结成蛛网。
刀起,血落,一刀断去凡俗念想,从此与子嗣无关。
撕心裂肺的痛蔓延至四肢百骸,身旁的孩子们痛哭流涕,哀嚎声此起彼伏,有人扯着嗓子喊娘,有人抱着伤口在地上打滚,像是濒死的鱼,在绝望中徒劳地挣扎。
可欢然没有哭,他只是死死地咬住下唇,冷汗打湿了鬓角,手指颤抖地抓着衣角,任由痛楚一点点吞噬他的意识。他不喊,不叫,不闹,等到能够撑着身子起身时,便俯身叩首,然后默默去打扫地上残留的血迹。
净身房的师傅勾起少年的下颌,审视片刻,轻叹一声:“真是精致的皮囊,可惜了是个男儿身,生在这宫里,迟早要被埋没。”
欢然不懂。他的脸色苍白,眼神澄澈如洗尽风尘的溪流,听了这话,只是轻轻地敛眸,不言不语。他不曾怨,也不敢怨,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那点微薄的月钱,和那些在心底偷偷计算的日子——等攒够了银两,就去打听母亲和妹妹的消息,再想办法回家。
可是,宫里分叁六九等,他只是微末小监。欢然的月钱总叫大太监们雁过拔毛。腊月里浣衣的手生满冻疮,浸在冰水里倒似红珊瑚雕的,廊下走过的小宫女嫉妒侍卫们都会青睐他的皮相,还要啐一口:“狐媚子托生的贱胚!”
直到他十二岁那年——深秋,冷得彻骨的时节。
那日,他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白玉杯,被老太监当场拖进角落,拳脚相加。对方的鞋尖踢在他腹上,力道沉狠,他蜷缩在地,喉间涌上一口腥甜,最终还是没忍住,唇边溢出一抹殷红的血迹。
苍白的脸被泥水沾染,狼狈不堪,衣裳褴褛,手指因疼痛而微微颤抖。
罚跪,是逃不过的。
寒冷的青砖硌得他膝盖生疼,冷风灌入单薄的衣衫,透过肌肤渗进骨头缝里,他的手指攥紧衣角,克制着不让自己发抖。
许久,他听见有人靠近的脚步声,稳稳地落在自己面前。
他下意识地低头,不敢去看来人。
那是一双上好的鹿皮靴,黑底金纹,纤尘不染,明显是这宫里的贵人。
许安平负手立在檐下,视线落在少年身上。
那是一摊狼藉的汤水,一个跪地不起的身影。瘦小,白皙,颤抖得像一只受惊的小兽,偏生生得极美,眉目低垂,乖顺无言,额角的血顺着鬓发缓缓滑落,触目惊心。
许安平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像是在打量一件新奇的玩物,忽然觉得,和他前几日猎杀的那只白貂有些相似——温顺,胆怯,不知反抗,却不知为何,越是这般,便越让人想要折磨。
他没有说话,只是随手接过身后侍卫递来的鞭子,轻轻一甩。
鞭梢破空而来,落在少年纤瘦的背上,衣裳裂开,一道血痕自肩胛蜿蜒而下,仿佛御花园新描的朱砂梅,艳得教人想拿银剪子连皮带肉铰下来。
他没有哭,也没有求饶,只是死死咬住下唇,伏在地上,一动不动。
许安平顿时来了兴致,缓步走近,微微俯身,声音里带着几分笑意:“喂,你怎么不求饶?”
少年伏在地上,额角的血渗进泥尘,染得脸色越发苍白。他嗓音极轻,几乎听不见:“奴不敢。”
“不敢?”许安平低低地重复了一遍,仿佛品味着这两个字的意味,忽然觉得有趣得很。他伸出手,指尖碾过少年唇上咬出的月牙印,逼迫他抬头对视,他的眼睛好似盛着半池将枯未枯的秋水,教人忍不住要掷块石子进去,看它究竟能漾起多少圈涟漪。
少年眸光微颤,眼底透着淡淡的恐惧,可更多的却是乖顺。他不会反抗,也不敢反驳,只会在鞭打落下时蜷缩着身子,静静承受,等着主人的兴致过去,才被施舍一丝怜悯。
和白貂一样,小东西雪白柔软,伏在猎人的掌心,瑟瑟发抖,却连挣扎都不敢,只会仰望着猎人,直到被亲手剥去皮毛,成了一件温暖的裘衣。
“你叫什么名字?”他随口问道,声音里带着随意的漫不经心。
少年垂眸,轻声道:“奴……欢然。”
“欢然?”许安平似笑非笑地重复了一遍。说罢,他随手丢开了少年,像是丢弃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转身对身后的侍卫吩咐道:“带回东宫。”
从这一刻起,欢然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他不再是宫中无名无姓的小太监,而是许安平身边的一只影子——一只温顺无害,却终将被主人玩弄至死的小兽。
跟在许安平身边并不是个好差事。许安平自恃皇长子、天之骄子的身份令他桀骜不驯,喜怒无常,甚至性情暴虐,稍有不顺便随意责罚下人。
茶水稍烫了些,便是一脚踹翻;守夜时打了个瞌睡,便挨上一鞭;射箭时未能及时将猎物捡回,当场就被狠狠扇了一耳光。
那些日子里,欢然的伤总是新旧交迭,手腕上鞭痕未褪,脸上又添了掌印,后背淤青未散,膝下已是血痕累累。他习惯了默不作声,也学会了在受罚时如何调整呼吸,以免因疼痛过度而昏厥过去。
他一直忍着,忍着,忍到夜深人静时,才敢在无人之处,悄悄地用手指摸一摸自己身上的伤痕。那些伤口密密麻麻,像是这宫里的规矩,在他肌肤之上烙下印记,一笔一画地提醒着他,这里是天家,许安平是他的天,而他不过是天底下最卑微的尘埃。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