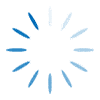果然,如周述所愿,许安平终于批准了他前往越州的请求。毕竟周遇等周家一大堆人还在京都,公主也在。这些年,周述已是朝堂上的影子,几乎把所有的锋芒都磨尽了。仿佛最低叁下四的一条狗,从不多数一句违逆的话,还挺会看眼色。
许安平也就大笔一挥让他去了。
周述走时,相思想要送他一程,但考虑到自己如今的身体状况,只能作罢。
周述离开后,日子似乎变得空洞许多。相思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读书上。她翻阅着史书,崔景玄的笔锋比御医的银针更利,那些墨字竟化作细密的银针,一针一针刺进肺腑里——易子而食的妇人指甲缝里嵌着黄土,饿殍枕藉的官道上飘着人牙子的旗幡,御膳房倒出的馊水里还浮着胭脂米熬的碧粳粥。
每当她翻过一卷书,似乎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这片土地上的痛与哀。她的思绪越来越沉,心中那份怅然无处寄托。
父皇在世时,虽然也有过些许风波,但最终总能平息,甚至还能下罪己诏安抚民心。
但如今,许安平的目光早已不再关心国家与百姓的疾苦,他的心早已被欢然占据。
她听闻,许安平竟为欢然建了一座名为“摘星台”的豪华建筑,台上堆满了各式奇珍异宝。欢然无意间提到,自己少时听说血玉髓美丽耀眼,自己未曾有幸得见,许安平便命令设立采玉监,强迫十万囚徒在毒瘴之地开采,甚至不惜让江水浮尸,纤夫的脊背磨出白骨。
那场景可怕至极,地方百姓更是饱受其苦,许多无辜的生命为此消逝。
相思闭上书卷,轻叹了一声,心中的苦涩无法言说。她低头提笔,字迹逐渐凝聚成一行行辛酸惆怅的文字:“
《临江仙·史牒惊心》
玉漏金猊春夜永,披衣细览芸编。人间冻馁有谁怜?朱门横绣毂,蓬户断炊烟。
千载兴亡成旧事,空垂珠泪潸然。瘴云湿鬓越州寒,忍听新雁过,岭月照孤眠。”
写完,又描绘了一幅小象,将画与诗一同交给盛宁,指示他送往周述处。
相思再次见到欢然是在一次阖宫饮宴之上。她本不打算前去,记得周述曾叮嘱过她,不必参与这些场合,但许安平那天不知为何突然神情兴奋,执意要求所有皇室成员到场。无奈之下,相思只得让连珠、盛宁跟随自己一同入宫。
宫中的气氛有些沉重,太后因病卧床,仍被许安平硬拉着入场,场面颇为不寻常。
许安平特意换了件簇新的玄色团龙袍,袖口金线在烛火下泛着冷光,倒像是把未出鞘的匕首抵在众人咽喉。
众人坐在大殿内,才恍若觉悟,原来这场盛宴不过是为了给欢然庆生。
那少年,依旧是那副文弱如纸的模样,眉清目秀,似乎随时都能被风吹散。他的确是主角,却依然不曾摆脱“侍从”之命,时不时跑到许安平旁边,斟酒捶背。
周围的皇室宗亲面面相觑,却又无人敢多言,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生怕这位情绪波动不定的帝王会突然生气,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相思觉得这大殿中的空气像是浑浊的浓雾,难以呼吸,便悄声对许安平说想去换衣服。许安平懒懒地摆了摆手,算是应允了她。她便借机离开,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处凉亭小坐。
凉亭外,太液池的水面微微荡漾,波光粼粼,清澈如镜。
相思心中不禁生出几分思念,思念着不知何时归来的周述,心中既有期待,又带着难以言表的惆怅。连珠走过来,为她拉紧了大氅。相思轻轻与她交谈几句,便见到欢然缓步走来,手中提着一尊精致的酒壶。
曾经相思对欢然不过是怀有一份淡淡的厌烦,厌烦他窝囊,也厌烦他天天跟在皇兄身后,奇奇怪怪得扭捏样子。而此刻,那种厌烦已悄然转化为憎恶。若不是他的勾引迷惑,皇兄也不会如此荒唐。
她皱了皱眉,心情复杂,只觉得眼前这个人是如今朝廷风气不正的罪魁祸首。
“奴见过公主。”欢然倒是主动迎上前来,行了个请安礼,语气温柔,依旧像个女孩子一样的温软语调。
相思默默端详着欢然,鎏金博山炉升起的沉香雾里,像是从青瓷仕女图上拓下来的影子。欢然的确精致,两道眉是工笔描的远山黛,把那张玉雪面孔衬得更似女儿家,杏核眼蓄着烟水朦胧的眸子,眼尾天然洇着薄红。
她缓缓开口,透着讥诮:“我没想到皇兄如此偏爱你。这些年,居然一直将你留在身边。就连贵妃都比不上。”
欢然低头作揖,眉眼间露出几分谦卑,说话时眼尾微微上挑,比池中睡莲更含露带怯:“能得陛下偏爱,实是奴的幸运。”
相思冷笑了一声,眼中多了一分冷意:“既然如此,你就应该安分守己,切勿恃宠而骄,劝谏帝王,勿扰朝政,不要让他与你一起胡闹。”
少时的黏糯乖顺也在不知不觉间有了上位者的姿态,满是审视与不悦。
欢然抬起头,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静静地望着相思,眼中似乎有一抹不易察觉的清澈光泽。相思顿时有些恍若隔世的感觉,仿佛自己曾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也在某个御花园的角落,看见周述时,是不是也曾这样毫无城府、赤诚坦荡地看着他?
欢然的声音打破了她的沉思:“公主怎知奴没有劝谏?”
夜风吹起少年身上宽大的锦袍,依稀间还能瞧见他手臂上新伤旧疤交错,恍惚间让相思回忆起许安平如何对他又打又骂的样子。
他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杂,相思始终无法清晰明了。
欢然话语温柔,像是细水长流的清风:“陛下圣心独断,又岂是奴一个卑微之人可以左右得?”他说完,又轻轻一笑,声音如同丝绸般柔软,带着几分满足依恋:“再说,奴只希望看到陛下开心。外面的那些事奴不懂,奴只愿意永远陪着陛下。”
五天后,许安平昭告天下:
朕即天命,万物从敕。御前侍中欢然,虽阉竖之身,然枕席殷勤,伏侍称意。今立为宸极皇后,摄六宫事,佩双凤金印,同享太庙。
朕既决,无需廷议。九卿有妄议者腰斩,史官敢非议者族诛。
其原有职衔如旧,另赐九锡,加万石。
钦此。
建武二年,冬末血日
许安平的行为,显然是激起天下民愤。
自古以来,男皇后之事从未见过,何况许安平的举动竟是如此公开与张扬,简直是在挑战天规。这一消息像把沾了蜜的匕首,先是甜津津地划开礼法金帛,待人们惊觉时,早已在宗庙社稷的肌理间剜出血淋淋的豁口。
太后因此病情再度加重,口口声声念叨着要亲手将这个逆子斩于剑下,多少次差点气得背过气去。她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但许安平依旧泰然自若,毫不为所动,反而开始筹备立后大典,宛如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
相思也是焦急万分,心如刀割。
许安平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撼动了国本,他不仅辜负了先帝的遗训,更是辜负了所有对大齐忠心耿耿的百姓。
她来回踱步,心中焦虑不已,连珠见状,轻声劝道:“公主,您若再这样焦躁,对腹中的孩子可不好。再者,驸马也快回来了。您要叁思而行啊。”
相思低头看了看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手指轻轻地触碰那柔软的曲线。那种微妙的感触,既是生命的跳动,也是情感的延续。她怀中的这个孩子,承载着自己和周述之间深厚的感情,也承载着她作为大齐公主的责任与使命。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她不能坐视不理。
她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翻涌的心情,终于沉声说道:“盛宁、苏禾,即刻送我入宫。”
“公主,”盛宁急忙劝阻道,“驸马爷早前曾说过,若没有皇帝和太后的召见,您实在不必前往宫中。”
“备轿。”相思的声音像是从冰河底捞出来的,惊得廊下挂着的鹦鹉都噤了声,面色也瞬间变得无比肃然,那张一直温婉柔和的面容,第一次展现出作为大齐公主应有的威仪与责任,“我身为大齐的公主,岂能眼睁睁看着帝王如此胡作非为?此事关系国运与社稷,关乎先帝遗志,岂容我坐视不管。你们不必再劝,我自有分寸,尔等不得违令。”
盛宁与苏禾见她态度坚定,无奈只得遵命,陪她一起前往宫中。
宫中气氛沉默压抑,内侍匆匆走来,焦急地低声说道:“皇帝正在批阅奏章,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公主可千万不要为难奴才们。”
相思直挺挺地跪在养心殿前的金砖地上,大氅铺展开来,倒似泼了一地浓墨。鎏金匾额上“中正仁和”四个字在细微的日光中泛着冷光。
“臣妹求见圣上。”
时间仿佛被拉得无比漫长,许久,紧闭的朱漆门扉突然泻出一线暖光,混着龙涎香的暖意蛇一般缠上她冻僵的指尖,屋内传来许安平懒洋洋的声音:“进来吧。”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