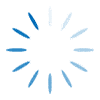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回到车上。看陶悦小口地喝果汁,陈原命令她:“你去给我买一瓶。”
陶悦嘟囔一句自己去,随即又加一句你怎么那么懒。
陈原感觉这句话自己对她说过。又不禁想,陶悦是故意的吗,她真记仇。
下一秒,脖子被揽住,陶悦柔软的唇递过来,温热的果汁渡到他口中,接着陶悦又喝一大口,跨坐在陈原身上,细细给他喂着果汁,大半瓶果汁喂完,陈原呼吸紊乱,手不自觉攀附在陶悦的脊背,他总觉得自己今天很奇怪,使不上力气,又觉得很慌很焦虑,觉得怀里的陶悦也没有实感,像抱着空气。
他下身硬得厉害,陶悦伸手拉开他的裤子,手掌覆盖在他的性器上,恶意地撸着。
欲望与心慌交迭,陈原不知道该顾哪个好,只能去找寻陶悦的嘴唇,像婴孩找寻母亲的乳头。她的吻是镇定剂,陈原刻意忽略掉内心深处软刺一般的异样。
几十秒的激吻后,陈原发觉自己已经全身都软绵绵如同躺在柔软的云端,心跳快得几乎失控。会这么兴奋,是第一次和陶悦车震的缘故吧。他这样想着。陶悦湿漉漉的吻从他的喉结一路向下,直至他坚硬的欲望被柔软与灼热包裹着。陶悦舔鸡巴的技术越来越好了,他很快就想射,在最后一缕晚霞消失,天彻底暗沉下来后,陈原终于没忍住射出来。射精后陈原觉得身体很重,手指无法控制地颤抖,感官失调,根本无法动弹,想说话,连舌头都无法动弹。
好想睡觉。眼睛几乎阖上的瞬间,陈原强撑着睁开眼,看着陶悦,她依旧跨坐在陈原身上,她在笑,是不怀好意的,有些得意阴冷的笑。像游戏里天性幼稚喜欢恶作剧的小女巫。
“你……”他只发出一个音节便再没力气。
感觉很奇怪。
直到一巴掌重重扇在脸上,陈原才勉强意识到什么。
一点都不疼,这巴掌根本不像打在自己脸上,仿佛打在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身上,或者说这巴掌是打在车座上的,他一点知觉都没有。
另一边脸又挨一巴掌,他连偏过头的力气都没有。想抬起手阻止陶悦,手指动弹一下便再没办法进行下一步动作。
“悦悦……”
已经猜到了。陈原却还是选择亲昵地叫她,而不是叫她的全名。
那些被下了迷药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反应。
陶悦哪里来的药。
那些隐隐的不安终于尘埃落定,陈原知道,这就是陶悦这几个月乖顺等待的机会。他确实对陶悦完全放松了警惕。从悬崖回来后。陶悦在虚光中的笑容与泪水,给他一种悸动的错觉。他彻底放下戒心。
陈原甚至想笑,嘴唇勾起微弱的弧度都这么吃力。
这个贱女人给他吃了什么?
是她的的精神病药物吧。陈原看过那些药的说明书,成分基本上就是镇定剂。所以,陶悦给他下了多大剂量,能完全把他放倒,但却还有意识。难怪心慌恐惧了一整天。被药物控制的感觉真恶心。
折迭刀被陶悦摸出来。刀刃弹开,闪着与她黑眸中相同的锋利寒光,下一秒被摁在陈原脖子上。
陶悦知道大动脉在哪里。她有小聪明,又愿意努力学习,初中学生物的时候,人体动脉和静脉分布图她能轻松画下来,后来也曾仔细地研究过人体解剖图,为精准地割开自己的动脉做准备。如今,可以用到陈原身上。
脖子上的动脉是最容易找最好割的。如果她现在手用力压下去,狠狠使力,只需要一个干脆的水平右滑动作,以这把刀的锋利程度,陈原的脖颈会像豆腐一样被轻易划开,皮肉翻飞,裂开软绵的血口,鲜血会争先恐后地喷涌而出,然后水龙头一般汩汩流着,不消片刻,这辆车将载满陈原的血奔向地狱。
用力下压的刀刃没入皮层,陷出一道血痕。
陈原抬起手覆盖在她持刀的手,虚握一下,又兀地垂下。
“别心软,悦悦。”
从什么时候开始,陈原就觉得,死跟活没区别。是盛月凝死掉的时候?宋倾遥推开他离开的时候?还是更早更早,他刚有记忆,被读不懂的恨意刺伤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随时会死,在参与斗殴的时候,在闯祸后被陈望岳主持家规的时候,在酗酒后飙车的时候。他一直热衷流连于生死边缘,以此找寻活着的实感。可惜祸害遗千年,他每次都死不掉。
可他从没想过会死在一个女人手中。女人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仇恨,最看不起的软弱生物。
陶悦真恨他。那双眼睛已经割开他的喉咙一万次了。
“你不敢。”
一如初次见面那样,陈原得意烂贱地笑着激她。
陶悦要是敢,这几个月,她有很多机会杀死陈原。当初机会摆在面前,她宁愿割自己的喉咙都没有拿刀捅他。
她怕杀人吗?也不全是吧。她此刻的眼神,仇恨而冷漠,充斥着强烈杀意。陶悦这种精神有问题的人,绝对有杀人的能力。但陈原认为比起杀人她一定更害怕被法律制裁。真该感谢法治社会,将他这个坏人保护得好好的。陈原想着,笑得愈发开心,身上仅剩的力气也随着他的笑开始溃散。他想就这样闭上眼,睡过去吧。可能再也不会醒来,昏迷后再被割喉,甚至疼痛都没有,多好的死法。陶悦对他可真好。
闭上眼之前,他回到那个悬崖上,与陶悦相视笑着。
这个骗子,竟然给过他那样美好的回忆。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