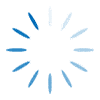沉孟吟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竟浑身汗湿着蜷缩在陌生的大床一角,半幅身子已然悬在床沿外,整个人摇摇欲坠,
意识到自己糟糕的睡相,她忙扭回到安全位置,摸了摸发凉的后颈,没来由后怕。
只差毫厘,她就会摔到床下。
当下的扭曲竟和梦里最后时刻的逃生画面吻合到严丝合缝。
梦中生死时速,她挣扎着从翻倒的车后座艰难爬出,一步之遥,却是用尽了她浑身的力气才得以脱身。
也是这一步之隔,火光四起,界定了阴阳。
她还活着...
回到现实的她骤然起身,环顾四周,房内只有两盏昏黄的台灯作为仅剩的光源。
视线转向灯光明亮的浴室,磨砂玻璃上映出的一道高大的身影,又隐约听到水声,她的意识才一点点归位,倏地反应过来是沉谕之回来了。
双眼焦距还模糊着,她奋力坐起来,揉了揉额角,缓和每次因为做到相同梦境后引发的轻微缥缈感。
双脚落地,踩到柔软蓬松的质感,一时间竟没站稳重新跌回床沿,这才发现自她下床的半圈,包括床的另一半领域内都整齐铺满了各色大大小小的抱枕靠垫。
噩梦缠身的冷意转瞬被这座另类却又令人心安的柔软城堡暖化。
她静静坐在床沿边,望着那轮没热气的上弦月发呆,等着脑中激荡的画面消散,也等着自己趋于平静。
沉谕之还真没见过一个人的睡相能差到这个地步,抱上去几次就滚下来几次。
准确来说是砸,还是头先着地的那种,且乐此不疲。
眉头皱着,嘴唇抖着,浑身冒着冷汗,像只受惊又莽撞的小鹌鹑。
喊不醒,也捂不热。
他很快明白过来,她该是深陷噩梦中无法抽身,类似鬼压床,除非启动自主意识剥离,否认外人怎么紧张也都无济于事。
但不管如何,至少在他怀里,由不得她再继续进行“自杀式”砸地。
他就这么抱着她,从卧室走到客厅,搜罗了一屋子的靠垫抱枕,暂时搭了座安全屋,静静围观了一会儿,发现这招可行,才腾出时间洗漱。
匆匆洗完,身上只擦到半干,还淌着热气,只潦草裹了条浴巾,他就急着先来看沉孟吟的情况,深怕她琢磨出新的自毁模式。
好在,人醒了,还知道乖乖坐在床边平息,应该是缓过来了,他悬在喉咙头的心终于放下了。
只是那道背影看着孤独又可怜,需要他花点心思抚慰。
他倒了杯温水,递到她手里。
沉孟吟苍白的唇动了动,嗓音嘶哑,没吐出完整的音节,但看唇形是在道谢。
对上她朦胧又恍惚的睡眼,像是刚从一个癫狂的世界死里逃生,茫然又无助地找寻现实中存在的意义。
水杯攥在手心,根本没顾得上喝一口,但整个人脱水得厉害。
沉谕之拿回杯子,扶住她的下颌,拿捏着力道,一点点灌进去。
干燥的唇舌被润泽后激活,沉孟吟的视线恢复了对焦,只是与目光平行的是精瘦有力的腰腹肌肉,她下意识舔了舔嘴角,淡淡笑着,“你回来了。”
说得可怜巴巴的,像她真的在这儿等他似的。
沉谕之轻嗯了声,指腹蹭掉她唇边的水泽,紧绷的五官柔和下来,捧着她的脸,仔细端详着那对红肿的眼睛,温声哄着,“照片和音频都是假的。”
沉孟吟却像没听见似的,拍了拍身边的空位,神色倦懒,“给我靠会儿。”
沉谕之坐下来,带着她的头枕到舒服的位置。
沉孟吟闭着眼,鼻尖是他沐浴后的淡香,脸颊枕着温暖结实的肩头,依稀还能感受他有力的心跳,浑身舒坦。
“你跟我说说话,随便说什么都好,”她小声请求着。
“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哭?”沉谕之问得直接。
“没哭,抹清凉油的时候揉进眼睛里了。”
沉谕之分得清真话假话,眼下这句是真话,但不是他想听的真话,微沉的嗓音里渗出蛊意,带着微烫的呼吸浇着她的耳轮,“但我听到你心里不舒服。”
沉孟吟勾勾唇,“心里也没什么不舒服,就是有点...不爽。”
沉谕之进一步引导,“既然随便说点什么都好,就没必要藏着掖着。”
沉孟吟支起身子,原本沉静的眸底涌起黑潮,冷冷一笑,那双狡黠又狠厉的眼睛分明像是在对他挑衅:你确定要听?
沉谕之嗅到了熟悉的攻击性,捏了捏她的下巴,左右晃动,“你什么样我没见过。”
沉孟吟顺势垂眸下去,下一秒,一口咬在他的虎口,下口狠,獠牙毕露。
沉谕之也不急着抽手,眼波似水,任由她发泄。
这套架势他早已司空见惯,凭她这点劲道,咬破皮都费劲,更遑论只是逞强。
沉孟吟小试牛刀,发现他不为所动,松了口,眸底冷着,“你没见过的时候多了。”
沉谕之挑挑眉,“说说看。”
沉孟吟不装了,也不演了,“是我给老头下的毒。”
沉谕之没给半点反应,淡淡嗯了声,“做得挺好,下手干净利落。”
沉孟吟持续加码,“我...当年是我利用你脱的身,害你被老头流放...”
沉谕之佯装无趣,逗小孩似的揉了下她的头,“说点我不知道的。”
沉孟吟没跟他开玩笑,拍掉他的手,继续加码,“我其实一点也不关心阿芸的死活,只不过是借寻她的由头让林清平入套。这样的我,你不会觉得很冷血么?”
沉谕之有的是话等着她,“老头在医院躺着是死是活我也没在意过,沉司衍还被我废了另一条腿。”
言下之意,要比冷血,你还不够格。
他的话貌似也没毛病,但沉孟吟依旧觉得这场交流两人不在同一频率,垂下头去,心里乱着,搓着手指,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述。
沉谕之却听得明白,侧身过去,吻了吻她的额角,“我的错,怕你习惯性会选择逃避,又怕说了你也不信,所以一直以来没把话说明白。”
沉孟吟眉心皱起,扭头过去,一脸不解,“什么?”
沉谕之捧着她的脸,一字一句,认真道,“我爱的本来就是全部的你。”
他的眼睛里有个黑洞,因为这句话的铺陈开来,正在一点点餐食她的意志。
沉孟吟躲着他眸底赤裸的炙热,却又不可避免被灼烧了脸颊和耳根。
良久,才小声问道,“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
沉谕之笑出声,平时看着挺聪明的人,一到关键时刻就当机,伸出手指,弹了下她的脑门,“我有没有受虐倾向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什么时候开始陷入的二元论的死胡同,自己都没发现么?”
沉孟吟微怔。
“冷血,不冷血?好人,坏人?用这种局限性的定义评判自己,是不是太单调了?”
沉孟吟被他问倒了,不想承认当下受他的话冲击很深,支吾着,“我...”
“好,那我换个说法,”她很快收拾完思路,重整旗鼓,“你会不会只是因为对于过往的不甘和执念所以才一时冲动代入是因为爱?也许你看到的我是隔着不真实的滤镜的虚影,又怎么确定自己是想打碎这面滤镜,还是想拥有滤镜下的人。”
“哦,原来我们现在是要讨论配得感和内耗的问题,”沉谕之点了下头,起身来到书架,背对着她,语气松弛淡然。
他的指节在高低起伏的书堆里随意跳跃着,很快锁定目标,抽出一本书,重新坐回来,放在到她手边,冲她努努下巴,“这就是我的答案。”
沉孟吟念出书名后扔到一边,“西西弗斯神话?我讲真的,你能不能别绕弯子。”
沉谕之双臂后仰,撑着床面,眉眼舒展,“这就是我的答案。你不是说这本是可以列为你最爱的书前叁,当时还兴高采烈抱着这本书对我说,这本书最让你迷恋的观点是关于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世界的反抗,坚持创造意义才是抵抗虚无的唯一法门。”
“恰好我们都喜欢利用心理和周遭环境来操控境遇冲破荒诞,那么选择佩戴怎样的面具演绎怎样的剧情就是我们抵抗虚无的手段。既然明确自己的所求所想早已冲破虚无,那么愿意让我们倾注时间和心力的所有人事物早已无关执念。”
他的掌心贴向她的心口,“打破滤镜,我只需要一击即中报复完闪人,欣赏你的狼狈足矣;而想要拥有滤镜下的人,我就需要调动全部的心力想你所想,及你所需,坚持在你虚无的世界里创造我存在的意义。”
“否则,你又凭什么需要我?”
“换句话说,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该是我应该内耗的问题,你应该拳打脚踢来反过来质问我,而不是自我怀疑...”
沉孟吟颊上飞过一团嫣红,没有哪一刻觉得这狗男人说服力这么强过。
她有些慌,也有一种多年积压心头的碎石被一举击溃的淋漓感。
也怪她曾经有一阵分享欲爆棚,又苦于无人可说,只能把那些散乱又膨胀的想法都向他倾吐。
但现在细细想来,无端引起她的分享欲,恐怕也是他的目的。
分享欲加深了亲密感,天长日久,更会滋生依赖。
沉孟吟尚在细细咀嚼他话里的内涵,沉谕之的唇已经贴了上来,隔着浴巾下躁动的物什也跟过来戳着她的肚子,“语言交流结束,现在试试用身体说话...”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